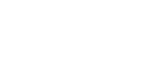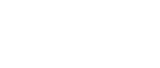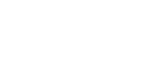王晓明:“L县见闻”|天涯·温故
| 招商动态 |2016-08-03
天涯微信号:tyzzz01
天有际,思无涯。
L县见闻
王晓明
八月中旬,随同事去大别山腹地的一个小村子住了一周。时间虽短,毕竟有见有闻,有一些因此而起的明白和疑惑。这里先写出几段。
L家湾
我们去的地方是在L县中部。出县城三十多公里,汽车驶入一个狭长的山谷,左边是连绵的稻田,右边是一条近百米宽、清浅、露出大片沙质河床的大河。河上,隔个一里半里的,就会横一段宽约三尺、以水泥和石块混合砌成的低坝,充当过河的道路。我们在其中一段坝边下车,脱鞋,从坝上涉水过河,再沿一条泥路上行七八分钟,就到了L家湾,一个三十来户人家、有一百五六十人的小山村。
村子依坡势南北展开。大多数是泥砖房,黄褐色的墙面、灰黑的瓦顶。一面墙上写着:“华主席在五届人大庄严指出:……”村子中央,有两幢新起的平顶楼房,其中一幢特别新,不锈钢的窗栏在阳光下闪亮,但是门窗紧闭,一条老黄狗懒懒地伏在门口。村人说,这家主人在外地打工,房子是他为自己娶媳妇造的,花了四万多元。“他还没有找到老婆呢!”村人笑说。
我住的那一家,是在村子的东北角,一座也是依坡势而建的两进的房子。第一进是原先的泥砖老屋,如今拆掉一半北墙,造成一个不大的、能遮雨的前院;二进是住屋,大约七年前造的,用了新式的空心砖,却依旧是平房,斜顶,老派的农家样式。屋子面南,正门进去是堂屋,左右另各有一间房,堂屋后面是厨房,有一扇门通向屋后。整个房子高而敞,据我在屋里目测,从水泥地面到屋顶足有八米高。跨出后门两三步,就是一面相当陡的山坡,它从北面和东面,构成这房子的院墙。
屋里屋外,处处显着主人的勤勉。堂屋的北墙下,是一台新买的二十九英寸的彩色电视机,机上覆着的红色的人造丝巾,被小心地撩起来,避免盖住散热的气孔。厨房的烧柴的灶台面上,贴着白色窄条瓷砖,擦抹得干干净净。前院里,贴墙砌了一口养鱼池,十余条本地特有的小鱼,静静地停在池底。池对面是一个单独的灶台,上架一口烧猪食的大锅。另一边叠放着两口寿材,结结实实,给年长者一种安心的感觉。前院东边开一扇小门,跨过去,是一个在山坡的斜面上辟出来的狭小的东院,其中以石块围成一个半米高的猪圈,卧一头圆滚滚的黑猪,小眼睛紧紧地盯着你。一群半大的母鸡,就在这前院和东院飞上跳下,伸着脖子“咯咯”地叫唤,却并不一定是下了蛋。屋后的山坡上,树木青翠,豇豆架、丝瓜藤,还有一小片竹林,其中一根竹子不知何故弯了下来,三四只中年母鸡,稳稳地停在上面,悠然四望。前院和后院都砌有排水沟,后院里还有一个专门洗衣用的方形石槽。最让主人自豪的,是在后山上打出一口四米深的水井,再以钢管和水龙头将水分别引入厨房、鱼池和洗衣槽。看我这城里人很节省地从厨房的储水槽舀出半碗水——这可是清澈甘甜的山泉哪,他笑了:“多舀一点,这是不要钱的。”
天刚蒙蒙亮,窗下两只小公鸡就扯开嗓门啼起晨来——其中一只还是哑嗓子,叫不成调,却异常顽强,远处每有一啼,它必要跟着叫一回。我干脆起身,随同事去后山走走。同事是本村人,四年没回来了,一上山就叫起来:“嗬,这山上林木都长好了!”四年前可不是这样,树木被人伐得七零八落,到处露出砂石的地面。“现在倒是一片绿了!”我四面看。“是呀,人都去打工了,村子里没那么多人来砍柴伐树了,这山就自然长好了……”他说。
确实,L家湾也好,周围的几个村子也好,凡我所见,尽是五六十岁的老人,和七八岁、十来岁的孩子。也遇到几个青年和壮年人,不是神色有点迟钝,就是缺一截胳膊,或者有别的残疾。似乎大多数体格和头脑健全的青壮年,都如那个造了楼房空关着的人一样,去城市打工了。我住的那家的一户邻居,有一个十八岁的姑娘,衣着鲜亮,一脸聪明相,完全不像是村里人。一问才知道,她已经在县城打工多年,是因为有人提亲,才临时回来的。我那同事的两个妹妹,也都是从上海回来不久,她们的丈夫,现在都还在上海打工。
山村人晚饭吃得迟,趁着天还没黑,我拎一把竹椅坐在堂屋口,问起主人的日常生计。他年近六十,身材不高,瘦,笑起来满脸皱纹,却一头黑发,不显老。和村里其他人不同,他能说一口流利的普通话,此刻就扳着手指头,慢条斯理地告诉我:平时家中,就他和妻子两个人,儿子在上海工作,两个女儿也都出嫁了,住在不远的外村;他种两亩多地,一年两季,每季可收稻子近千斤,以目前的粮价,扣除种子、肥料、雇短工的费用,每亩可得四百来块钱,一年合计一千五百元左右;这笔钱包括一年的口粮,油盐酱醋,还要用来交纳税、费——去年是一千多,今年减了,将近九百元。
“那你怎么够啊?”我的数学虽差,也立刻估摸出,他种地的收入不敷日用。“养猪——”,他妻子,个子矮小,终日在家中忙个不停的,解释说:每年养两头猪,一头春节时自用,另一头长到两百斤,卖了近千元;还有鸡,将近三十只鸡,平均每天可得六七个鸡蛋,每个卖三毛五分钱。“这样可以维持吗?”“不行”,男主人摇头,“现在农村办什么事情都要送礼,小孩满月、老人过生日、上学、结婚、造房子…… 一送起码几十块。”到他这年纪,似乎不用再为子女的教育费钱了,可是,外孙和外孙女们都在读书,现在学费这么贵,做外公外婆的,能不支援一点?毕竟是渐入老年了,总要生病的,医药费可是无底洞…… 说到这儿,结论很清楚了:如果没有儿子从上海接济,这家人的生计是艰难的。
“在村子里,我这样的境况属于中等。”他补充说。
镇上
从L家湾沿公路东行一里路,就是X家坳镇,原先的乡政府(现在已撤销)所在地。两长排新旧不一、样式各异的两层或三层楼房,分列在公路两边。凡是新建的两层房子,一律蓝色玻璃、铝合金窗、白色的外墙砖。百米左右的距离内,几乎每一家楼下都是商店:杂货铺、理发店、农用物资供应站、药店…… 竟然还有两家照相馆!“哪有那么多照相的生意?”知情人告诉我:“平常是没什么人上门,他们主要是做附近学校和学生的生意。”倒也是,报名照、证件照、毕业照…… 没想到乡村的学校教育还能连带着撑起这样密集的照相业。
两家肉铺子,都将案板摆到了公路边。“老板,多少钱一斤啊?”“八块!”“这两个一样价?”我指着并放着的一条蹄膀和一块肥膘肉,“都是八块!”卖肉的中年妇人一边挥赶苍蝇,一边回答。怎么比上海的超市里还贵啊?据当地人说,这还算便宜的,到了春节时候,要卖到十块钱一斤呢!
肉铺背后是镇上最大的“供销商场”,它和其它小货铺不同,用的是开放式的货架,一副超市模样。货架上花花绿绿,尽是包装粗劣而艳丽的仿制品。一盒三块多钱的饼干的包装袋上,印着一大堆龙飞凤舞的西文字母,中间四个汉字:“法国风味”。统一牌的冰绿茶,三元一瓶,差不多是九个鸡蛋的钱了,比上海我家附近的超市贵好几毛。商场的东墙上,高高低低挂着几排衣裤,仔细一看,大半是印着各式西文的T恤衫,和这里那里磨白了、剪出了窟窿的牛仔裤,要是光看样式,真是和大城市里出售的衣裤差不多。
在X家坳,更能显出城市化的气象的,是那差不多紧挨着的“中国移动”和“中国联通”的“专营门市部”。在统辖L县的H市的大街上,悬挂着一条横幅:“热烈庆祝我市移动用户突破五十万”。而在L县的两千多部手机中,多数是用的联通的号码。X家坳附近的山区公路上,不止一次有巨大的蓝底白字的广告牌迎面而来:“成功人都用全球通!”现代城市生活的潮流,在这条短短的山区小镇的街面上,声势逼人。在X家坳的东端,一幢老楼房正在装修门面:高高的大理石铺就的台阶,占满整面外墙的镀铬框的大玻璃窗,黑色大理石的柜台和地面,闪闪发亮的不锈钢防盗栅栏…… 大门上方一排粗大的英文字母:Credit Cooperation of China(中国信用合作社), 那突兀而豪华的气派,让我一时不知道身在何地。
三里畈。这是L县东南部的一个大镇,当地税务分局的朋友说,这是全县最富裕的一个镇。我在镇上粗粗走了一圈,只见好几条长街上,一家挨一家的,都是小商铺。印象最深的,是那些卖摩托车的商店,嘉陵、本田、山崎,还有英国的Gerige牌——有一家商店门口扯着大字横幅:“英国Gerige摩托车向广大中国用户提供全面的服务”,各种型号济济一堂。据说,L县的摩托车有两万辆之多(全县人口是五十九万),其中不少是无照车,就那么在乡间的高低不平的土路上驰骋。有一晚,当地朋友用摩托车送我回L家湾,在漆黑一片中颠簸了将近十分钟,突然在一座桥头遇到警察查夜,那朋友正尴尬——一位年轻警察已经盯住了那个应该挂车牌的部位,从警车上又下来一位年长的警察,是熟人!于是寒暄两句,顺利过关。
镇西南的汽车站对面,竖着一块醒目的标语牌:“经济发展是硬道理,招商引资是硬本事,项目建设是硬成绩。”三个“硬”字,将当地政府对自己工作目标的理解,说得清清楚楚。旁边的一面三层楼房的外墙上,还有一幅更大的标语:“无女不嫁,无女不好,无女不宁。”镇上的朋友解释说,当地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影响到镇里的政绩,才刷出这样的标语来。可后来,在别的地方,我不断看到类似的标语(还有这样的:“严禁非法胎儿鉴定和选择性引产!”),在远离三里畈的一个公路的三岔路口,L县的计划生育局还专门立一块牌子,标明各种针对胎儿鉴定和引产的罚款数额,最高的一种是七千五百元,这就明显不是三里畈一地的问题了。看起来,要让官员真正出力解决一件事情,最好的办法,就是将它算进考核政绩的指标。
在镇上逛到一半的时候,看见一幢奇怪的巨型建筑,五层楼高,方方正正如一座城楼,外墙是白色瓷砖,顶上还有四根圆柱,撑起一个琉璃瓦的翘檐式屋顶。“哦,那是镇上一个富翁的家,想进去看看吗?没关系的!”陪同的税务朋友挥挥手,领头走进那大屋。“请上楼,请上楼!”看清来人是谁,主人满脸堆笑地招呼。是四十来岁的中年人,瘦瘦的一张黑脸,将我们迎入二楼客厅,“我这里每天都有客人!……”客厅足有五六十平米,铺着地砖,中间一圈木沙发,西墙立两个一米多高的瓷花瓶,空空荡荡。主人是一个煤商,从大同贩煤至本县。“老板,生意好做吗?”我问。“不好做!能源紧张,煤价太不稳定了……”“大同的那些小煤矿……”“我的煤都是从大矿采购的!那些小矿的煤质量没有保证,我不敢进的。”大概是有税务所的人在,主人很快就把话题扯开。听说我们来自上海的大学,他立刻讲起自己儿女的教育问题:“我有三个儿子一个闺女,一人一层楼!……大儿子书读得不好,在省里一个专科学校念书。……老三不错,以后去上海读大学!我是文盲,没文化……”
我不习惯他讲起“我有三个儿子……”时的那种骄傲——在今日农村(也不止是农村),子女的数目已经成为贫富差异的重要标志,起身告辞。煤商陪我们下楼梯,在转角处的窗口停下,指着楼后面的一块足有一亩半的空地,和空地尽头的两排平房:“这都是我买下来的。我这楼房的地面,和楼前面的地(至少半亩),也是一起买下的。”“要一大笔钱吧?”“总共十四万。”这么便宜?税务朋友看出我不大相信,出了大门就向我解释:“要招商引资啊,就送土地给人家!”他还告诉我这样一件事:某投资客以八十万元买下镇上一家破产的小工厂,作为回报,镇里以每亩一万元的低价将工厂周边的二十亩土地卖给他。投资客挂出一块“××股份公司”的招牌,象征性地摆几张办公桌,一分钱生意不做,也一分钱税不交,却转手以八百万元的价格,将这些土地抵押给银行,空手赚进七百万!“瞎搞!”事情过去快一年了,税务朋友说起来还有点气忿忿。
“那你不查他的账?”朋友不好意思地解释:“我们这里小地方,不正规,那些人,”他指指周围那些两层或三层的自建住宅,“都没有账的,我们只能大致估算一个税额,然后每年递增。他说没有生意、亏本,我们也很难查……”这朋友是个重友情的人,遇见朋友,空口能灌下两杯白酒。虽然当了税务官,是非却没有忘,有一次酒酣耳热,当着同事和我们的面,他大声说:“我们是不怕的,我们有法律,就是县长来说情,也没有用!”可是,遇到那样的投资客,他却毫无办法。
从X家坳中学到L县一中
X家坳中学距L家湾不到两里路,是同事初中时(1980年代早期)的母校。在L家湾附近的公路边,我两次看见一辆车头贴着写有“X家坳中学欢迎你”的大红纸的小面包车,匆匆驶过。当天下午,同事来邀我了:“去X家坳中学看看吧?他们今天开学……”我有点纳闷:才八月中旬,怎么就开学了呢?
从公路向右转入一条砂土路,穿过一片稻田,就到了学校。果然是开学了,三层的主教学楼挂着横幅,几个工人敲敲打打地在一间学生宿舍里安装货架——这里要改成一个小卖部。校园西头,一个大玻璃窗的新食堂即将竣工,镀铬的门窗框的保护纸撕得七零八落。两长列带有廊柱的平房,是男生宿舍,墙漆剥落,锈红色的铁皮木门上写着粉笔字:“高一(2)”。大礼堂还是如二十年前那样,排满了双人木床,“我就在这里面睡过”,同事回忆说,“七八十个人一间!”和以前一样的还有厕所,灰顶,一排小方镂空窗,高踞在靠北的坡上,其中的光线和气味,二十年没变。
同事昔日的一位老师,学校语文教研组长,热情地招呼我们去主楼的校长办公室喝茶。他五十岁上下,皮鞋,挽着裤管,似乎不怎么习惯说普通话,但我大致能听懂:这两天忙得很!要和别的学校抢生源(我立刻想起那贴着红纸的小面包车),所以提前开学,计划招四百人,今天来的一半还不到!过两天老师们再分头到村子里去找,还会再来一些学生的,但计划大概完不成……
我问起学生这两年高考的成绩,语文老师略一迟疑:“考进专科的在内,超过百分之三十了。”“那另外的百分之七十的学生,明知道自己考不上的,他们读书的情况怎样呢?”我紧接着问。“也一样学啊,他们大部分还是希望能考上的,不然就不读高中了。也有一些被家长硬送来读的,就在学校里玩……”说到这里,他深叹一口气,“起码有百分之六十的学生的家长,到外面打工去了,不少是父母都在外面的,家里没人管,这些学生的心理成长有问题啊!”
三十多岁的校办主任也被拉来了,一口相当标准的普通话,说起学校的财政状况,直皱眉头:“学校需要的经费当中,县财政拨款只有三分之一,其它的?向银行借呀,寅吃卯粮!再就是靠学费了,高中?一学期连学杂费是两千元…… 不过,我们教师的工资是按月发足的,八月发七月的,也是寅吃卯粮!就拿我来说,中级职称,”他的语气有一点骄傲,“每个月能拿到一千二百块!”“在这里算高的吧?”我试探地问。“是。别人要少一点,一千块左右。”
“×主任!那边……”一个职员模样的人急匆匆进来,满头是汗。我们不好意思再耽搁他们,就此告别。晚霞笼罩的校园里,三三两两的都是新生,有端着脸盆在水龙头边洗衣的,也有一个人坐在台阶上发呆的。个子似乎普遍比上海的同龄人矮小一些,花花绿绿的T恤衫、牛仔裤,一个淡青色衬衣的女孩子,染一头黄发。
校门口竖着一块木板的告示牌:“校园卡……,成本费三十元。”在上海,我所在的大学的附属中学里,这种中学生必买的校园卡是免费提供的。L县的银行厉害。
走在回L家湾的路上,回望那渐渐隐入暮霭的学校的主楼,同事感慨万分:“我读书那会儿,这学校不错的,被称为县里的四中,有很用心的老师,可惜现在都去了县一中!乡下的孩子再不能就近读好的学校了……”
这话似乎也不完全对。X家坳镇上,就有一所“民营”的“楚才学校”,任课的都是附近几所中学的最好的老师,听讲的也都是从这些学校选送来的成绩靠前的学生。砂土地操场,一幢灰色的旧教学楼,二层楼梯的转角处,立着一面长方形的“正衣镜”,镜框两边分别写着:“每日三省可以正衣冠,晨昏颂读可以正人心”,仿佛与校名呼应,颇有一点气势。八月中旬,上海还在放暑假,这里却已经开课了,三十多度的气温,教室里坐满了人,热气直溢出窗外。我看了一楼的几个教室,在黑板前比比划划的,都是三十来岁的男教师,神情自信,手势和声音都很大。同行者中有刚从上海某重点中学毕业的,仔细看了黑板,说:“除了英文,别的课程一点都不比我们学的容易。”
本地的熟人介绍说,这里的学生,大多仍将学籍挂在原来的学校(例如X家坳中学),在这里读完了,再回学籍所在的学校参加中考或高考。“那学费怎么交?”“当然要高一点了,一般高中,每学期的学杂费,加上生活费,不到两千元,这里是两千七八百元。另外,‘楚才’向学生学籍所在的学校,每人付一百元。”民营学校在资格上受限制,不得不曲折行事,这我能理解,可是,那些学校怎么肯听任自己的优秀教师在这里上课呢?在教学楼的入口处,挂着一块小小的黑色大理石铭牌:“世界银行资助项目单位”。这么一个自己都不大能堂堂正正招学生的民营学校,居然拿到了世界银行的资助?真是拿到了,为什么铭牌那么小?我更觉奇怪了。
直到离开L县的那天下午,在县城第一中学,我才解开了这个疑问。县一中的一位老师听我谈到楚才学校,咧嘴一笑:“那不是民营!那是几个公立学校合起来办的,用民营的名义,集中好的生源和老师,提高升学率,也可以多收学费……”原来如此!那些骨干教师,其实是各自学校派出来的。L县一直是贫困县(脱贫还不到两年),那些合办楚才学校的公立中学中,完全可能有一所曾分到一点世界银行的资助款,既要用这个名目,名义毕竟不大正,那块大理石铭牌的小尺寸,也就可以理解了。“那么,有没有真的私人投资的民营中学?”我问。“有啊,西门就有一所,可老板不敢大投入,师资和硬件都差,招不到多少学生,你才开张,报不出升学率,一般家长自然不敢送子女来…… 据说去年亏了一百万!”
说到高考升学率,最硬气的自然是一中了。我们一进学校的主楼,劈面就见一张大表格,覆满了整整一面墙,上面密密麻麻列着被各地高校录取的本校毕业生的名单。第一至第三格分别是: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引我们参观的教研组长语气十分自豪:“我们每年都有一两个学生考进清华、北大的!考取本科的比例?百分之九十以上!”
一中的气氛的确不一样。校园中心是一个标准尺寸的椭圆形操场,修整得干干净净。隔着操场正面相对的,是红砖墙面的四层的旧教学楼,和用六百万元新造的五层的主楼——因为用了香港富商邵逸夫的一百万元,所以也叫“逸夫楼”。敞亮的大食堂的入口上方,四个大字:“膳食中心”。东北角的女生宿舍,是用教师宿舍改建的,粉红色的马赛克外墙,细格子的不锈钢防盗栅栏,网住了从一楼到顶楼的所有门窗和阳台。是午后一点多钟,太阳火辣辣地晒下来,校园里满是学生,眉清目秀,夹着书本匆匆而行,一会儿都不见了。“也是提前开学了?”我问教研组长。“是,已经开学了。放假也晚,整个七月都上课的。”他又笑着补充一句,“这里不大管教育部的那些规定的。”
作为L县升学率最高的学校,一中显然不愁生源。教师的收入也不错,据说教毕业班的,一年能有三万元。教师的办公室外面停了一长排摩托车,其中有一辆本田牌的,漆色鲜亮。但是,学校仍然缺钱,“县里的拨款只能满足学校的一半需求,剩下的一半,就要靠自己想办法了。”教研组长说。办法之一,就是办在学校边门五十米之外的“育英学校”。老师都是一中的,收费则视学生的中考分数而定,比一中的录取线低五分的收多少,低十分的又收多少。平均下来,高中生一学期的学杂费是五千元左右(一中是两千元,一点不比上海的名牌学校少)。“伙食费呢?”“一般一个月两百块吧。”我一算:“那在育英学校读一个高中,要花三四万哪!”
尽管如此,许多想进一中而进不了的学生,还是去了“育英学校”。“这和上海一些重点中学的做法差不多了。”我说,“是呀,你政府不给钱,叫我们怎么办?”教研组长头点得理直气壮。
出于职业兴趣,我每见到一个中学语文老师,总要问他:“你的学生课外读些什么文学名著?”在X家坳中学,得到的回答是:“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它的不大读。”那位老师进一步解释,“语文是比较空的东西,真要学好,考出高分,很难的,同样的精力放在别的课程上,效果明显得多——这一点学生都知道。”别的几处地方,回答也都是如此。不过,在一中那幢红砖楼的一楼东头的一扇门边,我却看见钉着一个绿色的小木箱,上面写着:××文学社投稿箱。
乡镇书店
三里畈有四家小书店。三家是私人的,格局差不多,单间的门面,却很深,两排长书架,靠近街面的都是簇新的“教辅”书,靠里面的是别的书——所谓“别的”,主要是文学类,《安娜·卡列尼娜》、《池莉中篇小说选》、《三国演义》……“老板,你这些书,”我指着文学类的书,“卖得快吗?”“不好,销不动的,没什么人买……”连着两位老板都这样回答。看我神色有点失望,陪同的那位税务朋友说:“我在旁边,他们都不会说实话的,怕我加税。下一家你自己去看。”果然,第三家的老板,一个看上去才二十出头的小伙子,回答得很爽快:“有人买!附近中学的学生来买,我一般四、五月份进书,到第二年春节,总能销掉两万块钱的书!”一年能卖出一千多本文学类图书,有这么多?
第四家挂着“新华书店三里畈营业所”的大牌子,我老远就看见了。可走近一看,那大牌子下面的主要的门面,已经用来卖服装了,旁边剩下的一间,才是书店。书架上稀稀拉拉没多少书,几乎全是“教辅”类,一侧的一个格子里,倒是有几本文学书,其中一本是《普希金诗选》,封面上一层灰,翻到版权页一看,竟是1986年出版的,定价:0.86元。
我去过的另外三个比较小的镇,包括X家坳,都各只有一家小书店,而且都挂着新华书店的牌子。情形也都和三里畈的那一家相似,门面相当宽,却几乎都只是卖教辅书。最典型的是X家坳的新华书店营业所,很大一间铺面,差不多一半的地方都堆着教材和教辅书,捆成一个个纸包,从地上码到一人多高。中年的女店员(承包人?)从空荡荡的柜台后面走出来,很勉强地应付我的问话:“我们是国营的!你是哪里的?大学老师?我有什么好担心的!……”最后,见我问个不休,她索性截断我:“你把身份证拿给我看看!”
幸亏我只遇到一个如此警惕的人。在中学的教室和宿舍里、路边的商铺中、同事的亲戚家,我都有机会从容地了解学生日常看些什么书。在L家湾附近一个村庄的兽医站里,主人见我对放在柜台上的课本发生兴趣,就进里屋又捧出一叠来:“这也是我儿子的。”不用说,所有这些场合,我看见的全是课本和教辅书,惟一的两本非教材书,一本是《红楼梦》(就放在那个兽医站的一叠书的最上面),另一本是当代作家路遥的《人生》,封面上都清楚地印着:“教育部推荐中学生阅读书目”。
在楚才学校的一间空教室里,我逐一查看那些整整齐齐摆放在课桌上的书簿,发现每一叠都夹着不止一本教辅书,我立刻想起了X家坳新华书店里的大堆的纸包,和X家坳中学那位语文老师的话:“我们这里……主要还是读课本上的那些文章,其它的不大读。”我更记起了三里畈的那位年轻的书店老板,当我问他:“都是学生来买你的文学书吗?老师们呢?”他笑了,仿佛是安慰我一般地说:“老师也有来买的。”
天堂宾馆
从L家湾依盘山公路往东北走大约七十里,有一处名叫薄刀锋的山岗,松林茂盛,山虽不高,但沿一里多长的山脊走一遍,还是很有些险峻的感觉的。在朋友W的陪同下,我们也去爬了一次,还得他照顾,住进了薄刀锋下的天堂宾馆,“是这里最好的宾馆!”W介绍说。
宾馆果然不错,背山而建,前面正对一个向下展开的山峡,峡中用坝拦出一个水库,水面碧绿。我们是傍晚到的,宾馆的餐厅里人声鼎沸,不断有人来和W打招呼:这是×镇财政分局的×局长,那是L县税务局的×主任,那边一大群,是H市里来的…… 都是熟人。
天黑了,当地的一位局长——朋友W的“铁哥们”——在宾馆附近的一家小饭店设宴招待。饭菜摆齐了,我刚想伸筷子,主人和另一位陪者(当地的派出所长)却站起来了,高举酒杯——都是白酒啊,要与我的同事和W一干到底!这一圈刚完,门外约好了似的,又一个接一个进来端着酒杯的人——都是刚才打过招呼的熟人,笑嘻嘻地,但却是非干了不可地,径直向W伸过酒杯去。窗外漆黑,风里透着一丝寒意,我周围却是热气腾腾,热诚的眼神,红脸,不断擦汗,声音一个比一个响。朋友W偏过脸来,高声对我嚷道:“我们这些人,不喝酒的时候有正气,喝了酒有豪气,都是好朋友!……”
我是上海人,毫无酒力,对这样的不挟一口菜、先灌下几杯去的豪情,真是十分羡慕。不过,我也看出了,这样的豪气之中,还有别的东西在。一位也是从门外进来的敬酒者,四十来岁,长身白面,“在H市干税务的”,敬酒时就毫不掩饰地将一桌人分成了两等:和别人都是一杯见底,惟独对我那同事的两位旧同窗,如今是普通乡民的,他只瞟一眼,沾一下酒杯,就放下了,那两位本份人,则依然照规矩,一饮而尽。
酒酣饭足,一桌人三三两两往宾馆走。我身边是那位陪宴的高高的派出所长,看他三十岁都不到,却肥头大耳,胖得可以。“中国的老百姓就是素质差,不像人家西方人,以缴税多为荣!……”他很惋惜地摇头。忽然,一辆汽车亮着大灯在道旁停住,刚才饭桌上的主人已经坐在车里,说:县里的某稽查股长明天要来水库钓鱼,他现在下山去接,不能陪我们了……
我想起了上山前知道的一些数字:L县全年的地税是三千万元(国税是四千万元),县财政局另外还能收两千万元左右的税费(例如农业税);全县财政收入大约是七八千万元一年。财政、税务、县委和县政府机关可以发足薪,但统计局、档案局之类就只能发百分之六十了……
晚上,同事回忆起和朋友W在中学时代的情谊和志向,对他和他的铁哥们的现状很担忧:“这人都不坏的,可就是这么吃吃喝喝惯了,住宾馆、钓鱼……什么社会责任、远大一点的理想都不想了!”他停住不说了。我和他同时意识到,我们也正住在这漂亮的天堂宾馆里……
一个问题
我是带着一个令我深深困惑的问题去L县的。这几年,“三农问题”逐渐引起全社会的关注,从政府到学界,主流的声音也越来越雄辩:要解决“三农”问题,首先必须大量减少农民——依据欧美和日本的现代化经验,走城市化的道路,让大部分农民变成城里人。可是,大批民工涌向城镇,城镇的接纳却愈益吃力,由此引起的种种矛盾,又迫使人们意识到,中国今天的情况已经与当初的欧美和日本大不相同:人口基数太大,自然资源明显匮乏,又无国境以外的空间可以转移就业压力。如果大批农民放弃了土地,却进不了城市,他们怎么办?这个社会又怎么办?于是,另一个主张提出来了:中国农村必须创造出适合自己条件的发展模式,应该将很大一个数量的农民留在土地上,在乡村——而不是城市里——创造新的生活。以我这样的“三农”门外汉的见识,我是很想赞同这后一个主张的。国情的不同是如此显而易见,全面的城市化并不可取。可是,在今天,要让大批的农民安心留在农村,这可能吗?或者说,国家和社会应该做哪些事情,才能使这个可能成为现实?这就是我的问题。
在L家湾,我第一次真切地设想:倘若政府切实地扶植农业、保障农民接受教育和医疗的基本权利,像我借住的这户人家,也就因此可以靠种地和养猪维持日用,还略有结余,付得起去镇上理发、购书、买衣鞋的费用,不用子女特别从城市接济,那么,这是不是一种可以留住农民的生活?在有些方面,它当然不能和城里比,譬如交通、货币收入、文化信息、卫生条件(我这主要是指厕所,若论一般环境的干净,至少L县的县城和三里畈、X家坳那样的镇街,是远不如L家湾的)。可在别一些方面:空气、水、食物的质量、听觉环境、人均绿色植被、资源的循环利用,等等,它都明显占优。还有一些方面,例如劳动(综合体力和脑力两种形式)强度、时间的自由支配度,则是互有优劣,难以比较。如果我们相信,城市和农村的一般生活形态,本就应该是不同的,那么,以中国目前的条件,像L家湾这户人家这样的生活(当然是在那些“倘若”能实现的前提下),是否就能使许多农民安心,成为他们在乡村创造新生活的扎实的基础?
在L家湾附近的一个叫作T家冲的村子里,我遇见一位不到四十岁、个子瘦小的党支部书记。他曾和村里的其他青年人一样,去上海打工。大约两年前,村(行政村,由靠近的几个自然村组成)里的党员们不满原支书的工作,将他缺席选成了新书记,他就回来了,还当选为乡人民代表。他骑一辆摩托车,一身泥尘,脸上是温和而歉疚的笑容:“对不起,来晚了,我正在那边搞修路的事……”我早已听说,为了从县里争取一笔拨款铺这条路(T家冲尚不通公路),他瞒报数据,将这个行政村做成了贫困村,为此自己少拿工资——在L县,村支书的工资是和村民的收入水平直接挂钩的。他一年多前就搭架子造新房了,可到我去的时候,房子还没完工:没钱。
虽然神情有一点腼腆,他却很健谈,坐下来说了没几句,就向我们介绍他近年向乡政府提交的两个提案,特别是今年的提案:“农村有文化的人都走光了,留下的人文化太低,所以要教育他们,我们现在有‘村村通’嘛,所以我提建议,要进行文化和科技普及,上课,我在村里组织过,来的人太少,白天大家要干活…… 所以我现在计划把上课时间改在晚上,吃完饭以后、睡觉以前的这段时间。所以……”他近乎滔滔不绝地说着他的乡村建设的计划,一旁坐着的他的大哥却隐隐露出不屑的神情。同事说,十年前他第一次见这位青年人(那时还只是普通党员),就惊讶于他的“呆气”——以一般村民不用的书面语言,热烈地谈论改造农村的计划。“十年了,还是这样子!好人!”同事很用劲地说。
我不禁也很呆气地想:如果四处都有这样的人,如果他们的努力不断取得成功,农村是不是就会比现在多一些人气,能收拢更多的青壮年农民的心呢?
但是,L家湾同时又让我明白,有巨大的障碍挡在前面。首先是自然资源,正像那个早晨我们在后山看到的,只有大部分的青壮年放下锄头和砍柴刀,去城里打工了,裸露的山岗才能恢复生机、郁郁葱葱,这是不是就意味着,农村残存的自然资源已经无力继续承受如此庞大的人口,不论前途如何,大多数的青壮年农民都只能前往城镇?可是,与L家湾的生活相比,城里人的生活不是更消耗资源吗?
另一个是今日乡村的主流文化。文化的一个基本表现,是日常生活方式,而L家湾及其周边地区,衣、食、住、行,各个方面,都强烈地表现出一种嫌弃乡村、向往城市的趋向。似乎只有年纪比较大的农民(例如我借住的人家的主人),还基本保持——并且习惯于——农家的生活方式,年轻一代的农民,即便从城里打工回来,住在乡间了,他们想要过的,却是一种尽可能像城里人的生活。
在L家湾附近的两个村子里,我分别拜访过两幢平顶的二层砖房,主人都是从上海打工回来的。一幢造于四年多以前,除了水泥地面,几乎没有别的装修,二楼的房子大多空着,惟有主人的卧室是布置过的:一张双人床,两边床头柜,床左是窗,右边是一架双门大衣橱,正对床的,是一个差不多占满一面墙的组合柜——这正是十年前上海“新工房”里的通行样式。另一幢则刚刚造好,磨光地砖面的客厅,瓷砖墙面的厕所,所有门窗都装着木质护套,一律是上海流行的“咸菜色”!尤其引起我注意的,是客厅一角的塑料垃圾桶,套着黑色的塑料垃圾袋——完全是城里人的派头了。
不用说,这样的生活方式是更费钱的。就以垃圾来说,我借住的那户人家,全部生活垃圾一分为二:可食类——包括鱼骨头——统统倒进一个大桶,煮成猪食,非可食类(从瓜子皮到纸药盒)铲进灶膛,充当燃料。因此,墙角一支扫帚,加一把农用铁铲,所有垃圾都处理得干干净净,连畚箕都不用置备,又何需花钱去买垃圾袋?当然,也很有可能,那新楼房里的塑料桶和垃圾袋,基本上是个摆设,日常的大部分垃圾,还是用农家的方式处置,并不真如大城市居民那样,每天换一个新塑料袋。但是,惟其如此,年轻一代农民选择生活方式时的这种一边倒的情形,就更加重了他们的实际生活负担:在这些新砖房里,不实用的文化符号式的物品,岂止是一个塑料垃圾桶?
不用说,新一代农民的这种选择,是社会教化的结果。在L县,我目力所及的范围内,几乎所有的新事物:镇上的建筑、商店里的货架和商品、公路上驶过的汽车、家中电视机播出的图像,更不要说县乡两级的大小公务人员——他们越来越多地将住家迁入城镇,也不必说L县以外的更大范围里的政治、文化和经济时尚了,一切都在刺激和布告农民:什么田坎、农舍、牛栏、猪圈……统统是粗陋的、落后的、必定要被现代世界淘汰的东西!只有城市:镇上、县里、省城、上海、美国……那里才是现代的世界!高楼、汽车、装着空调的办公室、灯红酒绿的大饭店……那才是理想的生活!这个社会的几乎所有的文化产品:广告、电影、肥皂剧、小说、报刊的专栏文章、“学术”论文…… 都汇入了鼓吹城市化、鄙弃乡村生活的潮流,即便一些偏僻的角落里,偶尔会冒出一两样别式的创作(譬如刘亮程的散文),也都迅速被这潮流淹没,沦为“农家土鸡”式的点缀,使人们更安心于享受城市的奢华。在这铁桶一般的“现代化”、“城市化”的主流文化的包围和熏染之下,农民除了向城里人的生活看齐,还有别的选择吗?和许多城里人相比,他们反而更轻贱自己的生活。
这样的乡村主流文化的形成,乡村的学校教育是一个特别有力的推动者。在访问L县的那些学校、看着学生们的年轻的面孔时,我不止一次地问自己:这些学校到底对L家湾们有什么用呢?除了向年轻人灌输对城市的向往,激发他们背弃乡村的决心,除了将那些最聪明、最刻苦、最能奋斗的年轻人挑选出来,送入大学,开始那成为城市中产阶级的“灿烂前程”——这是一所中学大门口的标语上的话,除了以这些成功者的例子在其余的大部分年轻人心头刻下无可减轻的失败感、进而刺激他们寻觅其它的途径——从打工到贩毒——也涌向城市,这些学校还做了别的事情吗?在L县,我多次惊讶于村民对各种升学和高考讯息的熟悉,“那个学校不行,它的及格线只有……”“不对,它是二本里面排在后面的!……”类似的言谈,已经成为这些显然是要终老乡间的人们的一个聚谈的热点。如果一茬一茬的农民都是抱着这样的热忱,不惜勒紧裤带,要将孩子们送进学校;如果他们也和周围的邻居们一样,看见孩子从学校毕业、回来务农了,就觉得脸上无光、家门不幸;如果孩子们从小就被推入这样的背水一战的紧张氛围,在这氛围的潜移默化中长大成人,那么,无论最后是否高考中榜,乡村的学生们对自己的家乡,进而对所有的乡村,都不会再有真正的认同,甚至也很难有真正亲近的感觉的。
那样一种感受生活的能力——让你既能拥抱城市的丰繁,也能懂得乡村的富饶,既能惬意地享受城市的便利,也能安心地品味乡村的从容,似乎正迅速地从我们中间消失。这消失是如此广泛,不但在上海,也在L县。
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是经济上“小康”了,手里有点余钱了,农村的年轻人又会怎样呢?他们会因此安心于留在乡村,重新开始珍惜已经拥有的生活,还是相反,觉得自己离城里人的生活更近了,于是更加跃跃欲试,怀着更大的期望涌向城市?说实话,我是觉得后一个可能更大些。
在L县度过一周以后,我沮丧地发现,我带去的那个问题,非但没有获得答案,它反而更加膨胀,更加复杂了。“三农问题”并不仅仅是来自今日中国的经济和政治变化,它也同样是来自最近二十年的文化变化。这些变化互相激励、紧紧地缠绕成一团,共同加剧了农村、农业和农民的艰难。因此,如果不能真正消除“三农问题”的那些文化上的诱因,单是在经济或制度上用力气,恐怕是很难把这个如地基塌陷一般巨大的威胁,真正逐出我们的社会的。
如果事情真是这样,那么,我们该怎么做?
王晓明,学者,现居上海。主要著作有《刺丛里的求索》、《半张脸的神话》等。
本文原刊《天涯》2004年第6期。
唯一投稿邮箱:tianyazazhi@126.com
天涯官方微店现已开通,关注微信公众号后点击底部菜单栏选择购买。微信ID:tyzzz01
 招商热线:400-151-2002
招商热线:400-151-2002